對年輕人冷酷無情的「新香港」——大學學生報如何走向沒落?
「由做(大學)編委,到編委消失,真的見證着成個過程」。深宵時分,前浸大編委成員鄭卓伶(Chloe)說,當年一班編委做學生記者,在反修例運動現場採訪,今日眾人已各散東西,「以前做過校報的老總,都說自己失去追新聞的熱情了」。現時八大院校的編委有3間「斷莊」或停運、2間改名後繼續營運,港大《學苑》編委銳減至3人。這種窒息感,彌漫整個學界,Chloe慨嘆:「學校有必要趕盡殺絕嗎?」
《國安法》實施後香港傳媒生態劇變,《蘋果日報》在2021年6月被迫倒閉,半年後《立場新聞》多名高層被捕,同日宣布停運,數日後《眾新聞》亦停運。主流媒體紛紛倒下,八間大專院校的學生報編委組織也陷入消沉、停擺。
據《光傳媒》採訪及整理,浸大編委去年在政治壓力下解散,其後一年「斷莊」;城大編委亦告「斷莊」;教大編委會專頁已停止運作。而《中大學生報》易名為《大學社區報》,多次向校方申請註冊未果;理大學生會不被校方承認後,理大編委會隨後易名為《紅磚社學生報》。目前港大《學苑》編委銳減至3人,僅嶺大、科大編委會仍正常營運。
最先敲響「喪鐘」是浸大編委會,Chloe是2019年度的編委成員,她指政治審查4年前已悄然發生。2019年6月兩次大遊行後,Chloe寫了篇即時報道,引述時任協理副校長楊志剛在《明報》刊登的評論《「洋紫荊革命」的白手和黑手》,指他描述示威者為「訓練有素的黑手」,並將社會運動冠名為「洋紫荊革命」。結果,楊志剛寫信給編委,要求把報道下架。

校方要求撤回報道 斷資源「陰乾」編委
Chloe認為,副校長的行為如同「黑箱作業」,亦不想與學生進行任何溝通,「那刻是有點愕然,為什麼要私底下寫信來?難道他說下架就下架嗎?」最後,編委沒有理會這位協理副校長的要求,事情不了了之。
直到去年浸大編委主編的《浸報Jumbo》和即時新聞平台分別因刊出前立法會議員邵家臻專訪、沒有人出席浸大升旗禮的報道,校方再次施壓勒令刪減報道內容,更表明會阻止新一期《浸報Jumbo》出版。
時任浸大第54屆編委「楚鳴」決定集體總辭,發聲明指對於出版過的報道「問心無愧」,在拒絕刪除報道的情況下,寧可在任期完結前一個月解散,不願「苟延殘存」,批評校方沒有書面通知的情況下,撤銷浸大編委官方電子郵件的使用權。

翌日,浸大管理層對編委聲明表示「感到憤慨」,即日起中止校方與編委會的所有關係,取消編委會使用校內所有設施的權利,同時表明「對於有關學生的錯誤行為校方將啟動紀律程序」。
Chloe透露,她當時收到消息指校方會重點打擊編委會,沒想到在一夜間被連根拔起,「沒有了mass mail、沒有了會室,然後沒有了支莊,一切沒有了」。她在媒體上見到同學在最後一天把物資、舊刊物搬走,會室變得空蕩蕩。這班年輕人也失去了通宵討論題目、在嬉笑玩鬧間進行交流的地方。
言談之間,她感嘆「新香港」對年輕人的冷酷無情,「學校有必要趕盡殺絕嗎?連成員維繫關係的地方都沒有了,是不忍心的。編委室佔據我大學生涯很重要的部分,是陪伴和培育過自己的地方」。

自我審查 社運文章下架
浸大編委倒下後,其餘院校的編委在報道上變得更小心翼翼。2020年度中大編委關靖豐(Miles)在一年任期內,見證《中大學生報》年度「六四特刊」夭折。2021年編委一如以往製作六四專題,準備6月在網站、社交媒體刊登,至於印刷版本,編委們擔憂內容敏感而一拖再拖,懸而未決。
直至7月,銅鑼灣發生梁健輝刺警案,港大學生會幹事在評議會通過「哀悼」梁健輝刺警後自殺。其後4名學生被國安處拘捕及被控「宣揚恐佈主義」罪行。眼見警察以國安罪行拘捕大學生,Miles嘆道,莊員惟有忍痛終止出版「六四特刊」,更把網上所有2019年運動相關的文章下架,「我們莊員因這件事起過衝突,但現實卻讓人必須作出折衷的決定。」
Miles表示,自「六四特刊」緊急剎停後,編委會已經士氣低落。有不少同學相繼退莊,對於敏感稿題的爭論也無日無之,「的確會有期望落差,中間有一段很辛苦的時期」。然而,他很快恢復過來,惟有選擇理性和抽離地做下去,「調整期望落差,在有限空間盡做」。
現屆中大編委拒絕《光傳媒》記者的訪問邀請。

耗損:欠缺資金、被校方割席
據《光傳媒》整理,5間院校包括中大、城大、教大、港大、浸大已相繼宣佈和學生會「割席」,例如發聲明指「不承認學生會地位」、拒絕為學生會徵收會費、收回會址或拒絕提供聚集場地等。
作為學生會屬會之一的編委會,也失去營運資金,例如歷史悠久、政評足以撼動公民社會的《中大學生報》、港大《學苑》,還有做過不少2019年社會運動現場重要報道的城大編委「即時新聞部」。
翻查3間院校編委的網頁或社交媒體,不少新聞及專題僅剩餘網上版本,《學苑》對上一次出版刊物為2021年春季的《渡》,而中大編委主動由《中大學生報》易名為《大學社區報》,惟向學校申請註冊未果。

多名學生記者被控暴動罪
2019年城大編委「老鬼」劉彥汶直言,2019年社運時學生記者被捕,《立場》、《蘋果》倒閉,亦令愈來愈少人想做記者。她那一屆的編委,有學生記者因在衝突現場而被控暴動罪,未來《假新聞法》來勢洶洶,更不會有人想跳進火炕裏,「2019年社會運動期間,學務長、校方都會慰問編委有否受傷、情況如何,但你會見到這幾年,校方開始冷眼旁觀不同案件。這都令編委感到恐懼」。

劉彥汶見證着編委氣氛由熱轉冷。乘着反修例運動過後的餘溫,2020年招莊會尚有很多學生懷着熱忱希望上莊,最終12人透過「臨時編委會」方式延續新聞理想;惟《國安法》落實一年後的2021學年,兩場招莊會「風涼水冷」,僅3人希望上莊,最後因人數不足、專業性成疑,得不到評議會認可而「斷莊」,至今已懸空長達2年。
城大媒體及傳播系3年級生Cindy(化名)便是期望上莊一員,她透露傾莊過程令人失望,上莊向他們分享編委須定期「與學校高層會面」,就着每期內容進行「吹風」,瞬間撲滅她的熱情,「如果要處處受到制肘,已經違背了我上編委的原意」。

失落:失去學生報,我們失去了什麼?
「一切改變都是可惜的。這麼珍貴的學生運動遺產,卻漸漸無法留下來」。港大2016年度《學苑》副總編輯、現任如水協會理事長兼編委江旻諺說。
作為首位進入這份擁有71年歷史、重要學界刊物的台灣人,他見證着2015及2016年本土思潮最盛行的時期。多年以來,《學苑》和社會運動有着不可分割的緊密關係,跟進過李國章任命副校爭議、圍堵校委會事件、反水貨客事件等,旗下出版書籍《香港民族論》更奠定公民民族主義的論述。
他指,大學學生報一般立場更鮮明,有自己的傳統、關懷的議題,向學校、政權及體制傳達年輕人的聲音,「年輕人對社會變遷的觸覺是最敏銳的」。江旻諺體會過這種「由下至上」的倡議模式,「初生之犢不畏虎——他們沒有社會經驗、不是既得利益者,比較沒有包袱,自然會大膽討論不同議題」。

學生主導的倡議模式
Miles在中大修讀政治及公共行政系,作為2020年中大編委成員,他認為《中大學生報》的傳統是關懷弱勢社群、勞工議題。此外,編委也會監察學校內政,例如最新推出校董會改革的分析報道,指出改革前沒有公開諮詢、過程不夠透明等,亦解構校董會和市場的密切關係。
他更指出,相比起傳理系學生的校園刊物如《大學線》、《Varsity》等,中大編委學生報完全由學生主導,不需經過老師的審批,「他們更加有倡導性,有時會有政治評論及倡議」。他感嘆,若失去學生報,年輕人的自主聲音會漸漸消減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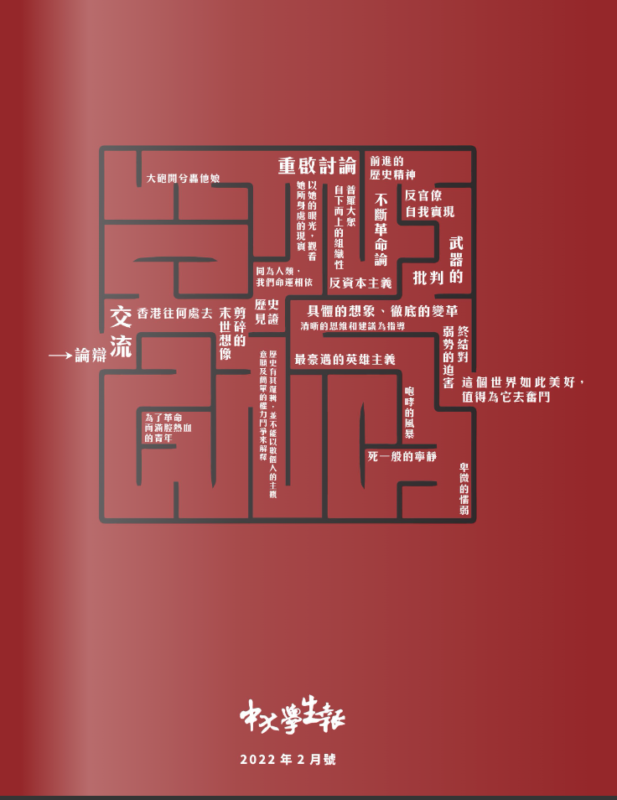
記者「木人巷」
Chloe於2022年在浸大新聞系畢業,她形容約8、9成同學都沒有從事港聞記者,選擇做人力資源管理、公關,或是體育、生活休閒類的記者。但在政治打壓下,曾做過編委的同學,不少人畢業後繼續做記者。
她就曾獲《香港01》錄取做港聞記者,惟最後回絕工作機會。現時她身兼多職,包括做 ASI 大數據的特約記者,有時接案寫藝術展、動物權益、社區重建等長篇專題,同時在《留下書舍》做店員。Chloe說:「有時真的很跳,但我不想為做正職而做。我覺得這個狀態是最舒服,起碼每一樣都是我自己喜歡的事」。
劉彥汶則指出,大學學生報猶如「試驗場」,給予她寫長篇報道的機會,也讓她看見主流媒體以外,其他公民媒體的可能性,「學生記者和獨立媒體的性質比較像,會報道一些少數及弱勢的聲音」。目前,曾任職城大編委的劉彥汶正於網媒《誌》 任職記者,喜歡公司的彈性和自由度,讓她可以深耕小眾的議題。
立志要做記者的Chloe,過往在《眾新聞》和《蘋果日報》實習時,遇過不少「元老級」記者前輩曾經做過學生報,讓她更希望朝記者目標奮進。作為浸大編委「老鬼」的她,也許下了一個小小的心願:「我經歷過那條路,我都很想有人可以行一次」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