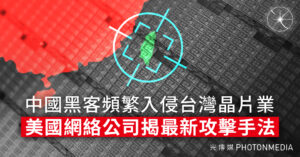2020年因觸犯《國安法》被通緝,兩年後因籌組「香港議會」再次被列入通緝名單,流亡兩年多的梁頌恆,說自己實際上被通緝了多少次,已數不清,「沒所謂喇,根本無分別」。
6年多前因衝擊立法會會議室,其後被判參與非法集結罪成,判囚4周。2020年年底出獄,由踏出監獄的第一天開始已被便衣警跟蹤,他覺得對方似是想告訴他:你已被嚴密監控中。而他亦只能告訴自己:也許這是最後一個可以離開的時刻。
被跟蹤讓他感到人身安全受威脅,但決定流亡,卻是關於整體社會氣氛,《國安法》實施後,他接受了幾間媒體採訪,有記者問他,支持獨立的立場有沒有改變。他覺得這是一個關於邏輯的問題,不會因為某條法例的實施或社會環境而改變。這些訪問,最後一個也沒有出街,當中包括一些現在已不存在的媒體,他說當時感到非常震驚,「《國安法》造成的寒蟬效應,原來可以這麼大!」
訪問「胎死腹中」,他覺得可能是媒體覺得報道本身有觸犯法例的危險,又或是為了保護他,但他感慨,其實結果也是一樣,「可以自由說話的能力,受到嚴重影響,即使我夠膽說,也不能刊出」。傳媒、公民社會相繼倒下,再加上被跟蹤,他做了一個無法逆轉的決定,就是離開香港。
離開是一種「尷尬」
他形容,自己的離開是一種「尷尬」,「作為本土派,身土不二,選擇離開是很尷尬的」。當時梁天琦還在獄中,黃台仰流亡德國,後來還有更多本土派人士流亡在外,他說身軀重要,但「香港心」更重要,「在世界上任何地方也能為香港做事,但如果沒有香港心,七百萬人留在香港也沒有意思」。他對自己說,如果能夠順利離開,一定要為香港做些事。決定到美國,也是基於這點,「在外的activist不多,從分工角度來看,華盛頓是一個必然的選擇」。
在華府的遊說工作,就如逆水行舟,跟國會議員見面,對方口裏說支持,心裏卻認為沒有迫切性,無需立即行動,「國會有這麼多法案要討論,香港的事早已不在首位」。沒有槍林彈雨的影像,他坦然國際社會對香港的關注早已退卻,世界上每一天都有大事發生,戰爭、天災人禍,排在香港前面的,實在有太多事項。
而他也逐漸看透,如果香港人要在這個極度資本主義的國家中扮演一個「game player」,就必須懂得這個金錢帝國的遊戲規則,「跟我當初想像的不一樣,香港人做政治,猶如『鄉下仔出城』」。
我們想像中的國際遊說,是以道德、人權狀況作理據,言論自由崩壞、大量政治犯、新聞自由萎縮。這些理應放在遊說桌上的,梁頌恆說經已失去效用,「已到達極限,2019、2020年可以做的都已做了,制裁要真正令對方生活受影響才有用」。作為流亡海外、做政策倡儀的人,他覺得遊說工作好像走到了瓶頸,「除非回到2019年那種狀況,但我不想再見到,相信很多人也一樣,我們也不能永遠用這個角度去做遊說」。
議會意義不大 重要的是民意授權
出了事,才能真正確認自己身份。他口中的那些事,是由9年前開始的社會運動,雨傘運動爆發那天,他不在香港,看着新聞片段,他跟自己說:「你應該要在那裏,因為你是香港人」。後來創立「青年新政」,確立自己作為本土派的身份,他說創黨成員之間,惟一共通點就是香港人這個身份。
組黨初期,他沒想過能爭取甚麼,後雨傘時代,他覺得很無力,民主運動無法推進,很悲觀,只想「搵啲嘢做」,組黨是一個實驗,他坦言,如果連佔領也無法改變甚麼,到底戰場在哪?說到底,「青年新政」的出現,只是由無力感催生的一種凝聚力。
2016年,他覺得是本土派的第一個高峰,梁天琦成功把本土思維帶入政治議程,而他自己也挾着民意,走進議事堂。宣誓被裁定無效,坊間謾罵四起,覺得他既然被選入議會,就不該玩這種把戲,但他覺得,整個制度本身就是無助爭取民主,「根本就是designed to be handicapped」。所以對他來說,議會本身意義不大,重要的是選舉,因為成功當選,代表着民意授權,「自己決定自己前途」的論述得到認同和支持。
離開「香港議會」
雖然他對香港的議會政治不抱任何希望,卻相信議會制度,流亡後參與創辦「香港議會」,他覺得香港人需要一個「載體」,重新把能量凝聚,這是民主運動必須的。但5個月後,他卻決定離開這個組織,離開的原因,他不願多說,只解釋,建立一個屬於香港人的議會,技術上不難,問題是用甚麼方法讓大家覺得有這個需要、為何要參與這件事,而且現時亦根本沒有一個可信的平台去討論。
「連可以在哪裏看新聞也困難,沒有媒體很難建立討論空間,香港公民社會已失去八成,海外又沒有替代的組織」。如何重建公民社會、如何獲得人民授權、如何達致共識,是他這些年不斷思考的事。
36歲,他說要規劃人生下半場,看着香港近年發生的事,他承認,自己處於疲勞狀態,但依然想「保持憤怒」,因為憤怒是一種動力,讓他繼續為香港做更多。對他來說,這個地方到底有甚麼意義,「因為有家人、戰友,那些一起作戰、成長的人」,雖然他說自己沒有思鄉,但因為被通緝而跟家人斷絕來往,有時也會覺得傷感,「為甚麼會變成這樣?」這是一條沒有答案的問題。
擁有相同的立場,並肩而戰,就是一個「想像中的共同體」。
他很想為「香港人」這個共同體努力,卻不時反問,「是否只是自己一廂情願的想像?」那時候,梁天琦被判入獄,黃台仰、李東昇離開香港,「他們被罵無義氣,香港人爭取民主,是要靠人犧牲去道德感召嗎?」他覺得,若只着眼於計算誰犧牲較大,民主運動是無可能成功的。
誰犧牲多一點?
「2012年『反國教』是中學生走出來,我們被感召,然後到了魚蛋革命,比前一次更大犧牲,才得到更多人走出來?我們還能夠犧牲多少?」他一直在說,無法停下來,「若是共同體,為何批判他們的決定?批判他們犧牲的多與少?」
這些問題,他反覆思考了幾年,直至反修例事件爆發,人們在七一闖進立法會的的?間,他覺得,香港人的確成為了一個共同體。香港人透過社會運動創造共同經歷,他覺得猶如一個「神話故事」,那些在街頭上一起經歷過的,任何人也無法改變。
「香港人」其實是個很新的概念,他說香港人在利益面前,都是「醒目仔女」,到底可以如何把香港人整體利益凌駕於個人利益之上,當然不容易,但他覺得一旦共同體的身份確立了,餘下的就是大家如何守護這個族群了。
近年有不少關於本土思潮的學術研究,但民間討論於2019年後近乎死寂,「完全無訪問、無人討論」,原因不言而喻。
離開侷促的牢籠,也許不是壞事,他可以繼續說想說的話,做覺得對的事,既然已進入人生下半場,何不改變軌道?他笑了,說是性格使然,自己是一個很執着於輸贏的人,而社會運動有一個明確的爭取目標,就是這一點擊中他。
「波馬」就是生計
因為喜歡博弈,到了華府後,他經營Patreon,寫「三經」:波經、馬經、財經。「沒有特別原因,純粹因為我懂這些,這些原本就是我的強項,如果要開Patreon,無理由寫一些自己不熟悉的東西吧」。而他不想寫政治,「寫政治論述,去到這個階段好像是『阿媽係女人』,我想提供有用的資訊,而『三經』是我興趣,研究得比較多」。
他的Patreon,訂戶分了三個層級,其中一項「你買Notes,我捐俾細葉榕」是最近開的,收益扣除平台手續費後,全數捐給細葉榕人道支援基金,「因為近來分享賽馬的notes,有幾次成績不錯,所以鼓勵讀者如果想跟,可以捐錢給細葉榕」。他承認,賽馬和社會運動的確是風馬牛不相及,「兩件事沒有太大關聯,所以如果贏了錢,有能力就希望幫到他們」。
沒有東西比生計重要,一個做遊說工作的流亡政治人物,也要交租吃飯啊。他笑說自己的生計,就是那些「炒賣的東西」,「『波馬』就是我的生計啊,我一直也是這樣維生的,對這方面的資訊比較理解,所以才有東西寫和講」。
博弈彷彿是他人生的基調,波、馬、股票是賭博,流亡難道不是一瑒未知結果的博弈?很有可能會輸啊,他當然知道,把個人命運連繫着一個群體甚或一個城市,是一場非常冒險的賭博,「但如果不努力去做,人還有存在意義嗎?」
梁頌恆小檔案 2007年 擔任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幹事會會長 2015年 創辦青年新政 2016年 出選香港立法會選舉並奪得議席,於立法會就職宣誓儀式期間時展示 “Hong Kong is not China” 橫額,並以英語讀出諧音「支那」,及後被裁定宣誓無效 2017年 被取消立法會議員資格 2020年 因2016年11月衝擊立法會會議室,被裁定一項參與非法集結罪成,判囚4周;同年12月流亡美國並因觸犯《國安法》而遭到香港國安處通緝 2021年 與流亡港人成立「Hong Kong Liberation Coalition」,從事政治遊說及支援流亡港人工作 2022年 7月與袁弓夷、何良懋等人成立「香港議會」,梁再度被通緝;12月辭去「香港議會」職務
相關文章
- 深度人物專訪離散把愧疚留給我吧 張崑陽2023-04-27
- 深度人物專訪離散午夜夢迴痛哭 走出傷痕確立目標 | 周永康2023-04-28