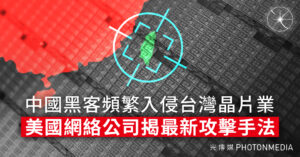34年過去,維園的燭光再也無法點起,曾經在六四晚會擔任司儀的列明慧,用舞台劇將記憶傳承下去,更授權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與台灣「曉劇場」把劇目《5月35日》帶到台灣。她說,每一次演出都像播下一些種子,希望把被壓迫者的故事帶到世界不同地方。維園晚會曾經還有前支聯會常委趙恩來,由15歲做支聯會義工開始,到今天已是中年。他說,死難者的歷史不應該在世界的記憶中消亡,記住這段歷史是這代人的責任。
2009年,列明慧做了多年維園燭光晚會主持,漸覺晚會雖然重要,卻有一定限制,「不如嘗試用舞台劇方式,或者能帶出更多?」於是就成立了「六四舞台」。當時她沒有想得太長遠,但《在廣場放一朵小白花》演出後,反應非常好,一年後重演。當時座上的觀眾不乏校長和老師,都覺得應該把關於六四的劇作帶入學校。
司徒華稱「六四舞台」值得做下去
她記得,已故支聯會主席司徒華也是嘉賓之一,「他說值得做下去」。一句「值得」,便是12年。由2009至2021年,「六四舞台」共製作及公演8齣舞台劇、295場學校巡迴演出,於2019年公演的《5月35日》獲第29屆香港舞台劇獎(Hong Kong Drama Awards)最佳製作、最佳導演、最佳劇本、最佳燈光設計、年度優秀製作等多個獎項,榮耀未及照亮舞台,布幕已徐徐落下。

曾經,她帶着不同的劇目走進校園,例如關於劉曉波或「黃雀行動」的故事,「你以為學生應該會知道某些事,其實未必,有些可能連SARS也不記得了」。她覺得,每一次演出,都像播下一些種子,雖然無從得知這些種子何時發芽,但十年堅持,卻是很好的公民教育。
那時《國安法》正準備實施,校園亦開始出現「舉報熱線」,列明慧說當時一些老師和校長跟她說,有些事情已無法在校內說,「他們怕跟有『煽動』風險的團體接觸」。她憶述當時有30間學校報名觀看巡迴演出,最後因為疫情及國安風險,全部決定取消。她感慨,「這就是香港現況」。
一個劇本也容不下的城市
「2019年前有沒有想過『六四舞台』會結束?當然沒有想過!」從前,她覺得劇場創作相對安全,但一切來得太快,她發現原來言論和創作自由,竟是那麼脆弱。那些關於「六四舞台」的訪問,她已無法在網上找到,有些東西還是避不了在一夜之間消失,但她沒有失望,說仍有不少人在夾縫中努力,說好這個地方的故事。

後來,她離開了,「很傷心,香港失去了太多」。制度崩壞、司法獨立蕩然無存,從前覺得翻牆、中國政府對待維權人士的手段,都是遙遠的事,事件霎眼來到身邊,「拘捕你,未審先關柙兩年」。而這個故事,還未完結,她說也許會變成台灣故事,「以前覺得六四是中國故事,現在變成了我們自己的故事」。
來去匆匆,她曾經感到傷感、恐懼,低潮期漸遠去,她努力爬起來,「幸運亦不幸,經歷過香港最璀璨的時間,現在香港有難,不能忘記依然留在香港受苦的人,各自在做能力所及的事」。例如近日在台灣出版《五月三十五日:創作.記憶.抗爭》,收錄六四舞台得獎劇本《5月35日》,除了廣東話劇本,書中還收錄了國語及英語翻譯劇本,以及劇作的創作歷程及相關評論。


但舞台劇的光芒,畢竟還是要在台上才能展現出真正的光芒,飛越香港上空時,她沒有帶很多東西,就是有這齣劇的版權,今年她授權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與台灣「曉劇場」把劇目《5月35日》帶到台灣,希望劇作能夠在不同地方、以不同語言上演,把這個屬於每一個母親、每一個被壓迫的人的故事,帶到世界不同地方。悼念死難者,亦哀悼那些逝去而又不能再被言說的故事。
執導《5月35日》 不能再到香港
「曉劇場」導演鍾伯淵覺得六四事件在歷史上,不只是中國的事,全球生活於極權統治國家的人,也可能要面對這種事情發生在自己身上,對於這種傷痛有着共感。故事講述一對年屆80的老夫婦,惟一的兒子30多年前「死於不自然」,到了今天很多問題依然無法得到答案。
老婦多年來期待從痛苦中解脫的一天,而一向膽小的老頭,卻愈想愈不忿,老伴即將離去,他覺得自己沒有甚麼要害怕了。二人定下目標:在5月35日這一天,堂堂正正地拜祭兒子。「在不正常國家的陽光底下做正常的事也是不合法的」,作品簡介寫道。

也許,台灣已是最後一個能演出此劇的華文地區了,鍾伯淵從前常到香港,執導此劇,他說已有心理準備日後不能再到香港,甚至是轉機。即使不能再到香港,他依然覺得必須把劇作搬上台灣舞台,因為他體會過極權對自由的打壓,那怕只是一張小小的貼紙也容不下。
2020年他到澳門過關時,被帶進房間拷問,要求他把貼在護照上的「Republic of China」的貼紙撕掉,「一直以來去世界各地,也沒有人要求我撕掉」。撕掉後,終獲放行。這次事件後,他覺得自由實在很重要,要繼續發聲,不能因恐懼而封閉說話的權利。
雖然作品寫的是六四,但他認為其實所有人也可以從劇本探討可能發生的傷痛,「透過這個故事,觀眾不只能感受曾經發生在1989年的事情,更是自己國家的歷史。近年我們探討的轉型正義,或許需要更長時間才能到達,但劇本中的母親等不到轉型正義,所以她只能到油燈將盡的時間,用自己的生命去照亮這件事」。
因國安風險 未有跟香港導演編劇溝通
演員梁德翔詮釋劇中那位母親時,則認為她尤如點亮一根火柴,一點很微弱的燭光,「她在彌留之際,只要往前一步,就是死亡,她說了這句話:即便這個光會滅,每個人的生命也會走到終點。無論是對自由民主、對愛的追求也好,又或是失去孩子的傷痛,她只想貢獻自己一點小小的光,就是一種巨大的力量」。
一個讓人反思極權、自由的劇本,已無法在香港公演,首度來台,劇團卻未有接觸香港的導演及編劇,鍾伯淵坦言香港現時的狀態並不樂觀,擔心若對方參與會有危險,所以當初獲得授權後也只跟「六四舞台」的負責人開會。他解釋,他們沒有明確地表達安全受到威脅,但香港人到底能如何活下來並繼續追求自由,鍾伯淵覺得現時處境變得愈來愈困難。

劇作將於本月2至4日共公演6場,全部爆滿,鍾伯淵說此劇在台非常知名,大家都很期待,很多人也想知道台灣劇團會如何呈現這個主題,「以及在這個議題下,跟當代可以產生甚麼意義和對話」。
那年,他才4歲,六四對他的意義就是看見爸媽,一邊看電視新聞一邊尖叫,「我們一家人對這件事印象也很深刻,在世界的另一方,有一班人在抗爭,非常震撼」。
而梁德翔當時已是初中生,事發翌日,同學們都在竊竊私語,大家有看新聞嘛?有沒有看到坦克人?她記得那時的補習老師是個熱血青年,會播《一無所有》的錄音帶給她聽。排演此劇,她曾經有一個關口無法跨越,女主角的悲傷,到底該如何詮釋?「她很悲傷,但不是對外的,所以情緒不能過份外露,(雖然)她在罵人,其實是自己的悲傷」。
港演員戴面具以廣東話讀劇 紀念是爭奪「詮釋權」之戰
國際特赦組織台灣分會秘書長邱伊翎表示,此劇已無法在港上演,所以能夠把它帶到海外演出是一件很重要的事。而這次演出,除了五場普通話演出外,還會有一場廣東話的讀劇,由香港演員戴着面具進行,「我們花了些時間去找讀劇的香港人,但他們的身份是保密的。想盡量保護他們,畢竟他們能演出已是很大的勇氣,但他們在香港還有家人,即使人已在台灣,但還是擔心會影響家人,所以不希望有太多曝光」。

無論在香港抑或是台灣,過去也有不少關於六四的意見,有人覺得悼念活動行禮如儀,亦有人會覺得這是中國的事,「大家會想,為甚麼要去紀念六四呢?但當這樣的活動也被港府和中國政府打壓、禁止談論,這樣純粹的劇場也被禁止,展現出港府對言論自由的打壓愈來愈嚴重」。
她指出,這樣反而引起更多人願意去了解這件事,愈是打壓,愈是團結。「以前大家會覺得,我又不是中國人,又不是統派,為甚麼要紀念六四?但現在大家都會了解紀念其實就是堅持人權價值,影響其他沒有人權的國家」。
人們都說,紀念就是拒絕遺忘,她覺得,記住六四,其實是一場爭奪「詮釋權」的戰爭,「中國政府也想搶這個詮釋權,其實六四沒有死這麼多人啊、天安門母親說的事情不重要」。中共一方面說沒有發生這些事,另一方面卻禁止談論,「如果覺得根本沒有發生,為甚麼要害怕討論?」
15歲做支記義工 2020年維園悼六四被囚8個月
2019年6月4日,前支聯會常委趙恩來在維園忙得不可開交,協助燭光晚會進行,他沒想過,維園的燭光從此不再照亮。他記得,那年的主旋律不再只是六四,反修例事件正在醞釀,「雖然是悼念六四死難者,但也很注重香港議題」。
第一次參與燭光晚會,他只是一個中學生。2001年六四12周年,他牢牢記着這一年,「死難者不能夠就此犧牲,要傳承民主的理想,把追求民主的理念延續下去,不能忘記這件事,希望更多人知道」。

趙恩來15歲加入當支聯會義工,他說當時是社運低潮期,作為學生,只是抱着好奇的心態,之後十多年,參加燭光晚會的人數每況愈下,「那時候沒有太多公民團體,大家也不熱衷參與社運,遊行示威有幾百人已好開心,跟2019年是兩個世界」。那時,他覺得點起燭光,是每個香港人的事,是最低成本的參與。
2020年,這件事再也不是「最低成本」,他跟其他支聯會常委,在維園點起燭光悼念六四,被控「煽惑他人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」和「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」罪成,判囚8個月。
他說,那年踏進維園綠色足球場,大台沒有了,但他還是看見很多熟悉的面孔。他說,這是多年的約定,一定要去,而當日出現的人,有堅持悼念多年的老人,也有一家大小,他沒有想過,以個人身份出現於某個空間,竟會被定罪。
「去之前,已有坐監的準備,當天幾萬人在維園,最終告了廿人,我只是代他們去接受這件事,但這是不公義的!」雖然被判罪成,他說自己並無做壞事,六四去維園「不是一件值得被罰的事」。

獄中遇見不同人物,別人問他因何「入冊」,他會說:因為我喺維園點蠟燭。他覺得很諷刺,「裏面很多像我這類的人,以可笑的理由入去」。可笑的事,竟成為現實。
輾轉來到2023年,當公開悼念變成忌諱,他覺得香港人這麼多年的參與,成為政權眼中的一根刺,「無論你承不承認,也不能無視這件事」。這是多年以來,整個城市累積的記憶,他說香港人容易適應不同環境,總有方法去守護這個理念。
「平反六四」是人生意義 當行禮如儀變成奢侈
如果要說人生意義,趙恩來說,一生人必須達成的一件事,就是平反六四,「但不是坐着就能平反,能力所及的事,就要去做」。對他來說,六四就是啟蒙,「他們以自己的生命讓我們了解沒有人權、自由是怎樣的一回事,所以他們不應在世界的記憶中消亡」。他覺得記住這段歷史是我們這代人的責任,六四其中一個啟示,就是在爭取民主的路上,不是說幾句社會就會改變。
曾經,有人認為燭光晚會行禮如儀,他苦笑,誰會想到,今時今日連行禮如儀也變得奢侈。那些昔日戰友,很多都已在獄中,「雖然有些事,做了好像沒有用,但他們堅持做,用行動證明『我不放棄』。能喚醒其他人嗎?他們未必care,只想做咗,無悔」。
老頭說:「我們就去衝擊,這條不正常的底線。」
老婦說:「老伴,我終於覺得你愛我了。」

相關文章
- 港聞六四26歲丈夫遭槍殺 天安門母親張景利:親人不能白死2023-05-25
- 港聞六四祭文述亡者故事:準新郎送喜糖被掃射死 女醫生拯救傷者中彈亡2023-05-25
- 港聞反修例後特首態度轉變 只在乎六四悼念是否違法2023-05-30
- 港聞建制社團6.4借維園辦家鄉市集 劉銳紹:試圖掩蓋六四痕跡2023-05-18
- 港聞前區議員接連收到國安處電話 查問會否辦六四悼念活動2023-05-25